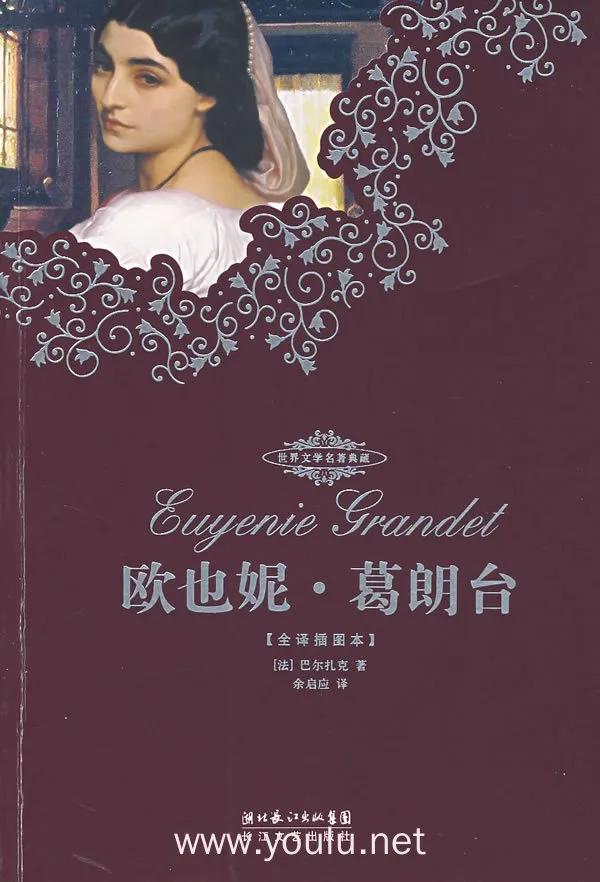伟大的盖茨比翻译(伟大的盖茨比小说翻译)
第八章
我整晚都睡不着,一个雾角一直在海湾呜咽。我在光怪陆离的现实和野蛮吓人的噩梦之间辗转反侧,像生了病。快黎明时,我听见出租车开上盖茨比家的车道上,我立马从床上跳起,开始穿衣服-我觉得有些话要告诉他,有些事要给他提醒,早上就太迟了。
走过他家草地,我看见前门还开着,他正靠在大厅里的一个桌子旁,因为沮丧或缺少睡眠而表情凝重。
“什么也没发生,”他虚弱的说,“我等到四点钟,她走到窗户,在那站了一会,然后关上灯。”
那晚当我俩在屋子里找香烟时,对我来说他的房子似乎从来没这么大过。我们打开帐篷似的窗帘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墙上摸索开关,我还撞在一架吓人的钢琴琴键上,发出哗啦声。说不清为什么屋里到处是灰尘,房间潮湿,好像很多天没通风了。我在一个不太熟悉的桌子上发现一个烟盒,里面有两支干巴巴不太新鲜的香烟。打开客厅的落地窗,我们坐下来在黑暗中抽烟。
“你应该走,”我说,“极有可能他们会追踪你的车。”
“现在走?老朋友”
“去亚特兰大市待一周,或者去蒙特利尔。”
他不会考虑这个,在他知晓黛西要干什么之前,他是不可能离开她的。他紧抓着最后的希望,我也不忍心让他放手。
就在那天晚上,他讲述了年轻时和丹. 科迪的奇怪故事,告诉我这个是因为在汤姆的恶意诋毁下,吉. 盖茨比这个名字像玻璃一样支离破碎了,长时间神秘华丽的表演结束了。我想他现在将毫无保留的承认所有的事情,但他却想谈谈黛西。
黛西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好女孩,在多个秘而不宣的能力加持下,他与这样的人接触过,但总感觉中间有铁丝网似的。他发现她极其性感,起初他和泰勒营的其他军官一起去黛西房间,之后是单独去。他非常震惊--以前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房间。但是让人紧张到透不过来气的是,黛西就住在这里,对她来说这房间稀松平常,就像他在外露营时住的帐篷一样。这屋子有种熟透的神秘,暗示楼上的卧室比其他房间更美更酷,门廊里正举办着喜气洋洋的活动,暗示没有霉味呈淡紫色的浪漫虽然已逝去,却新鲜而有活力,令人想到今年闪闪发光的汽车以及鲜花不会凋谢的舞会。许多男人喜欢黛西-这在他眼里增加了她的魅力,这也让他兴奋。整个屋里,他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,屋里还弥漫着那些充满活力情绪的影子和回音。
但是他知道,他出现在黛西房里是一种奇怪的偶然。虽然做为吉. 盖茨比,他的未来灿烂无比,但他现在是个没有过去、一文不名的年轻人,不知何时他制服上的伪装会从肩头滑落。因此,他要充分利用时间,贪婪肆无忌惮的拿走他可以获得的。最后在十月一个安静的夜晚,他占有了黛西,占有她只是因为他连摸她的手的权利都没有。
他可能会鄙视自己,因为他在虚假的借口下占有了她。我的意思不是指他做生意那非法的几百万美元,而是他故意给黛西的安全感 ,让她相信,他来自和她一样的阶层 --这样他完全有能力照顾她。实际上,他没有这样的能力,他背后没有一个舒适的家庭,他随时有可能被无情的政府随心所欲的派遣到世界的任何地方。
但是他没有鄙视自己,事情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发生。他大概打算拿着能带走的离开,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致力于追随圣杯。他知道黛西是不同寻常的,但他不知道一个“好女孩”是如何不同寻常。她消失在她奢华的大房子里,消失在她那富裕丰富的生活中,留给盖茨比虚空。而他感觉和她结了婚,这就是全部。
两天后当他们再相见时,是盖茨比紧张的喘不上来气,感觉有点被辜负了。买来的奢侈品星光熠熠,在她家门廊闪着光。她朝他转过身,柳条沙发时髦的吱吱响,他亲亲她那好奇可爱的嘴巴。她感冒了,声音有些沙哑,比平时更有魅力。盖茨比深深的感到财富所包含存储的年轻和神秘,许多衣服的新鲜感,闪耀如银想般的黛西安全而骄傲的处在水深火热的穷人之上。
“我没法跟你描述,发现自己爱上她我有多惊讶!我甚至一度希望她抛弃我,但她没有,她也爱上我了。她认为我知道很多,因为我知道许多她不知道的事情。噢,在那儿,我偏离了抱负,爱意越来越浓,突然我什么都不关心了,如果我有更好的机会告诉她我要做什么,那么做伟大事情有什么用处呢?”
他出国前最后的下午,他搂着黛西静静的待了很长时间。那是个凉爽的秋天,屋里生着火,她双颊红润。她不时的动来动去,他稍稍跟着调整下胳膊,他还亲吻了她黑色闪光的头发。那天下午有一会让他们感觉非常平静,好像为之后长长的分别他们留下深刻的回忆。她沉默着亲吻他肩膀的外套,或者他温柔的触摸她的指尖,她好像睡着了一样。在一个月的恋爱中,他们从未像那个时刻如此亲密 ,也从未交流的如此透彻。
他在战争中表现突出,上前线前他是个上尉,阿贡那战争后升为少校,掌管机枪营。战后他发疯似的要回家,但某些复杂的原因或误解却把他送到牛津。他当时很担心,黛西信里透露出绝望和焦急,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来。她感觉到外部压力,想看见他,在身边感觉到他的存在,确信自己做的对。
因为黛西还年轻,她那虚伪的世界,弥漫着兰花的芳香和令人愉悦、欢快的优越感,以及用新的曲调演绎生活中的忧伤和启示的管弦乐,为这一年的韵律谱了曲。整个晚上,萨克斯的演奏着比尔大街布鲁斯,数白双金色银色舞鞋拖着脚掀起闪着光的灰尘。在晚上,总有些房间因为低甜的狂热不停的颤动,光鲜的面孔到处飘荡,像被忧伤的号角吹落一地的玫瑰花瓣。
在这朦胧的世界,随着社交旺季的到来黛西又开始活跃起来。
她又重新每天和几个人分别约会。黎明时分,才瞌睡着倒在床上,晚礼服上的珠子和薄绸与垂死的兰花缠在一起,被随意丢在床边地板上。她心里一直渴望做个决定,刻不容缓的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,这个决定需要近在眼前的外力促使,因为爱情、金钱或者无可争议实实在在的东西。
在春天过了一半时,随着汤姆. 布坎南的到来,这个外力成型了。他的身份和地位都很有分量,黛西感到脸上有光。毫无疑问,黛西心里挣扎过,也解脱了。盖茨比收到来信时人还在牛津。
现在长岛已经黎明时分,我们把楼下其他窗户都打开,房间里满是渐渐发白渐渐金黄的光线。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穿露珠,幽灵般的鸟儿开始在蓝色的树叶上唱歌。空气中有一种缓慢怡人的动静,几乎没风,预示着是一个凉爽、舒适的一天。
“我认为她没爱过他,”盖茨比从窗户那转过头,挑衅的看着我。“你一定要记住,老朋友,她昨天晚上非常激动,他以那种方式说话,吓到了她,这让我看起来好像个不值一文的骗子。结果是使得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”
他沮丧的坐下。
“当然,他们结婚时,她可能会爱过他一阵子,即使在那时也是更爱我,你觉得呢?”
突然,他说出一些奇怪的话。
“无论如何,”他说,“这是我自己的事。。”
除了揣测他在这无法估量情事上的紧张程度,你还能想到什么呢?
汤姆和黛西还在度蜜月时,他从法国回来,用最后的军饷去路易斯威尔,这趟旅程凄凉而不可抗拒。他在那待了一周,在原来十一月的夜晚他们一起咔嗒咔嗒走过的街道,重游他们驾驶她的白色跑车走过的偏僻地方。正因为黛西的房子看起来总是比其他房子更神秘,更令人开心,因此尽管她已离去,他认为这个城市还弥散着忧郁的美。
他离开了,尽管感觉找的再辛苦点可能会找到她,他还是离开了,把她抛在后面。硬座列车上很热,他现在身无分文。他走到车厢连接处,坐在一个折叠椅子上,车站后退,陌生建筑物的背面向后移动。接着进入一片春天的田野,那儿有一个黄色有轨电车跟着他们跑了一会,上面的人说不定在某个街上见过她白皙美丽的面孔。
轨道是弯曲的,现在它跑向太阳的反方向,夕阳西下,洒满余晖,祝福她曾经呼吸与共、渐渐消失的城市。他绝望的伸出手,好像能抓住一绺空气,留下这个地方的某个片段,这一切因为她的存在而可爱。他泪眼模糊,一切都消失的太快了。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其中最新鲜、最美好的一部分。
我们吃完早餐,从门廊出去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。那天晚上对天气影响非常大,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香味。盖茨比前任仆人中的最后一位-园丁走到台阶下说:
“我今天把水排干,盖茨比先生,叶子很快开始落了,这样水管总有问题。”
“今天别整了,”盖茨比回答说,他抱歉的转向我,“你知道的,老伙计,整个夏季我从没用过它。”
我看看手表,停下来。
“我的火车还有12分钟开”
我不想去城里,不应当去工作,不仅如此,主要我不想离开盖茨比。我错过那辆火车,又错过一俩,然后我才走了。
“我会打电话给你,”我最后说。
“好的,老伙计”他说。
“我中午给你打电话。”
我们慢慢走下台阶。
“我想黛西也会打过来,”他不安的说,好像希望我确认似的。
“我猜也是”
“好,再见”
我们握了握手,我走了。到栅栏前,我想起什么,回头对他说:“他们都是坏人,你比他们加起来还要棒”。
我一直很开心对他说了这个,这是我唯一一次恭维他,因为从开始到最后我都不赞同他。他先是礼貌一笑,之后是那种灿烂会意的笑,好像在这件事上我俩一直是不谋而合。他华丽的粉色西装映衬在白色台阶上显得明亮耀眼,我想起三个月前第一次参加他的聚会时的情景。草地和车道上挤满了人,那些人猜测着他的不轨。他站在台阶上挥手,心里隐藏着不会腐烂的梦想。
我谢谢他的款待,我和其他人总是因为这感谢他。
“再见,我很满意早餐,盖茨比。”
在城里,我试着对冗长的股票做报价,接着在转椅里沉沉的睡着了。快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声把我惊醒,我满头大汗的站起来。是乔丹打来的,她这个时间带给我,是因为她行踪不定,在酒店、俱乐部或私人庄园,其他办法很难找到她。平时她的声音通过电话线带着某种新鲜和凉爽传过来,好像绿色球场上的一块草皮航行到办公室的玻璃窗上,但是今天上午听起来又哑又干。
“我已经离开黛西家了,”她说,“在亨普斯特德,今天下午要去南安普顿。”
也许离开黛西家是明智的,但这一行为惹恼了我,接下来她的话让我呆住了。
“你昨天晚上对我不好。”
“那有什么关系吗?”
沉默了一会,她接着说:“不管怎样,我想见你。”
“我也想见你。”
“要不我不去南普顿,下午去城里?”
“不,我想今天下午不行”
“好吧”
“今天下午不可能,太多-”
我们像这样交谈了一会,接着突然就都不说话了,我不知道我俩谁啪嗒一声挂上电话,但我知道我不在乎了。即使在这世上我再也不能和她说话,那天我也不可能和她一起喝茶聊天了。
过了几分钟,我打给盖茨比,但是占线。我打了四次,后来一个恼火的总机接线员告诉我说,线路正等从底特律来的长途电话。我取出时间表,在3.50那趟火车上画了个小圈。接着我靠在椅子上,理理头绪。那时刚刚中午。
当我早晨坐火车经过灰堆时,我故意走到车厢另一边。我猜一整天都会有好奇的人待在那儿,小男孩在尘土中寻找黑色血迹,一个唠叨的男人一遍遍讲述发生出事的经过,直到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不真实,讲不下去了,墨特尔. 威尔森悲惨的故事渐渐被人忘记。现在我想再倒回去,说说那天晚上我们离开后修理铺发生的事。
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她的妹妹,凯瑟琳。那天晚上她一定破戒喝酒了,当她到达的时候,她喝的有点傻了,无法理解救护车已经开往芙拉市。当他们让她明白这一点后,她立马晕倒了,好像这才是整个事件最不能容忍的。有个人,不知出于好心还是好奇,开车带着她跟在她姐姐尸体的后面。
午夜之后很久,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围在修理铺前面,乔治. 威尔森在里面的沙发上前后摇晃。起初办公室的门开着,每个走进修理铺的人都忍不住向里面张望。后来有人说这太不像话了,才关上门。米凯勒斯和其他几个男人陪着他,先是四五个,然后两三个。最后,米凯勒斯不得不让最后一个陌生人多等十五分钟,他回自己家,煮一壶咖啡。之后,他单独一个人在那,陪威尔森待到天亮。
三点钟时,威尔森胡言乱语、低声哼唧的状态变了,他越来越沉默,开始说起那辆黄色的车。他宣布说他有办法查出来那个黄色的车是谁的,接着他脱口而出说,两个月前他妻子从城里回来时,鼻青脸肿的。
但当他听到自己说这个,他又退缩了,开始抽噎着哭:“噢,天哪,”米凯勒斯只好笨嘴拙舌的努力分散他的注意力。
“乔治,你结婚多久了?好啦,试着安静的坐一会,回答我的问题,你结婚多久了?”
“12年”
“有孩子吗?来吧,乔治,安静的坐下,我刚问你问题啦,你有孩子吗?”
棕色坚硬的甲虫一直撞击暗淡的灯泡,只要米凯勒斯听到汽车在外面路上疾驰,他就感觉像是几个小时前那辆没停下的车,他不想进修理铺,因为工作台弄脏了,尸体曾躺在上面,他只好不自在的在办公室转悠,因此在黎明前他对这里面的每样物品都熟悉了,他还不时的挨着威尔森坐下,想方设法让他安静下来。
“你有没有一个时常去的教堂吗?乔治?就算你很长时间不去了,我可以给教堂打个电话吗?叫来个牧师和你聊聊,如何?”
“没入教”
“乔治,你应当去教堂,为这种时候做准备。你一定去过教堂吧,你不是在教堂结的婚吗?听我说,乔治,你不是在教堂结的婚?”
“时间很久了”
回答问题做出的努力打乱了他的节奏,这让他安静了片刻。和原来一样半清醒半迷糊的神态又重新出现在他无神的双眼中。
“看看抽屉里面,”他说,指着桌子。
“哪个抽屉?”
“那个抽屉,就那个”
米凯勒斯打开离他的手最近的抽屉,里面除了一根用皮革和银辫子制作的小巧贵重的狗绳外,什么东西都没有了,那根狗绳看上去很新。
“这个,”他举起来问道。
威尔森盯着它,点点头。“我昨天下午发现它,她想方设法和我解释,但我觉得这事情很滑稽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你妻子买的它?”
“她把它用薄纸包起来放在她的柜子里。”
米凯勒斯从中没看出什么古怪的事,就他妻子为什么买狗绳他给威尔森说了十几种可能的原因。但是,很明显威尔森已经从墨特尔那听过某些类似的解释了,因为他又开始小声喊:“哦,天哪!”还有几种解释没说出口安慰的人只好闭。
“那么一定是他杀了她,”威尔森说。他的嘴突然张大。
“谁啊”
“我有办法查出来”
“乔治,你是在胡思乱想,”米凯勒斯说,“你受刺激了,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,最好坐下来等到天亮。”
“是他谋杀了她”
“乔治,这是个意外。”
威尔森摇摇头,他眼睛眯起来嘴巴微微张大,不以为然的“哼!”了一声。
“我知道,”他坚定的说:“我一向是那种信任别人的人,不想怀疑任何人,但当我要了解什么时,我会弄清楚的。那个人在那辆车上,她跑过去和他说话,他没停。”
米凯勒斯也看到了,但他不认为那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他相信威尔森太太是从她丈夫那逃跑,而不是想去拦住某辆车。
“她怎么可能那样?”
“她城府很深的,”威尔森说,好像回答了问题:“啊,啊!”
他又开始摇晃,米凯勒斯站起来搓弄那根狗绳。
“乔治,也许我可以给你的朋友打电话?”
这是个没指望的愿望,他几乎可以确定威尔森没有朋友,他连老婆都对付不了。过了一会,他开心的注意到屋里有所改变,窗外渐渐变蓝,他随后有些开心。五点钟时,屋外天色更蓝,可以关灯了。
威尔森失神的眼睛转向灰堆,那儿小块的乌云呈现出奇异的形状,在黎明的微风中匆匆到处飘。
“我对她说,”沉默挺长时间后,他嘟囔着说,“我告诉她,她也许能骗我,但骗不了上帝。我把她带到窗户那,”他费力的站起来走到后面窗户那儿,脸紧紧的贴在窗户上,说,“上帝知道你做了什么,知道你做的所有事情。你可能骗了我,但你骗不了上帝。”
米凯勒斯此时正站在他后面,震惊的发现他在看T. J. 艾克博格医生的眼睛,那双巨大苍白的眼睛正从消散的夜色中浮现出来。
“上帝看见一切,”威尔森重复道。
“那只是个广告,”米凯勒斯忍不住提醒他,随即他从窗边转身,回头看屋里。但威尔森一直在那站着,脸贴在窗格处,冲着清晨的曙光点点头。
六点钟时,米凯勒斯累坏了,听到外面停车的声音,心里十分感激。这是头天晚上的一个旁观者,许诺会回来。因此,他做了三人的早餐,只有他和那个人吃了。威尔森现在更安静了,米凯勒斯回家睡觉,四个小时后他睡醒匆匆回到修理铺,威尔森不见了。
后来,他的行踪被追踪到罗斯福港口,接着去加德山,他在那买了杯咖啡和一个三明治,并没有吃,全程步行。他一定累了,走的很慢,因为他直到中午还没到加德山。到目前为止,不难计算出他的时间-有几个男孩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,几个司机看见他在路边古怪的盯着他们。之后的3个小时的时间,他就无影无踪了。基于他对米凯勒斯说有办法查明,警察猜测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各家修理铺以及周围打听一俩黄色汽车。另一方面,修理铺没人没看见他过来,大概他有了更容易、更可靠的方法查明他想知道的。下午两点半时,他在西卵村,在那他问人去盖茨比家的路,因此那时候他已经知道盖茨比的名字。
两点时,盖茨比穿上浴衣,给管家留下话说倘若有人打电话,就到泳池那给他送个信。他特地去车库拿个在夏季供客人娱乐用的充气床垫,司机帮他充上气。接着他指示说什么时候也不要开那个跑车出去,这有些奇怪,因为它的前挡板需要修。
盖茨比扛着气垫床,走向游泳池。中途,他还停下来调整了它一下,司机问他是否需要帮助,他摇摇头,一会消失在树叶正在变黄的树丛中。
没有任何电话打进来,但是管家没睡午觉等到四点钟,直到就算有电话来也没人接了。我觉得觉得盖茨比自己也不相信会有电话,大概他也不关心了,如果这是真的,他一定感觉自己失去了这个温暖的世界,怀揣一个梦想太久付出高昂的代价。他一定因为抬头从那些吓人的树叶里看着陌生的天空,而颤抖,正如他发现玫瑰长的多么怪异,照在稀稀拉拉草叶上的阳光是多么粗鄙时。这是一个全新的物质却不真实的世界,在那儿可怜的幽灵把梦想当空气一样呼吸,随意的漂浮着,就像那个灰色奇怪的生物穿过杂乱无章的树悄悄靠近他。
司机听到枪声,他是沃尔夫西姆手下的一个人,之后他只说关于枪声他没想太多。我从车站直接开车到盖茨比家,我焦急的冲到前面台阶上,大家这才感觉或许出事了,我始终认为,他们当时已经知晓了。司机、园丁、管家我们四个人,一言不发匆匆走向浴池。
当清水从一边放进来,流向另一边的排水沟时,泳池有一个非常微小几乎觉察不到的水流。涟漪很小几乎没有波纹的影子,承担了重负的床垫沿着泳池没有规律的漂动。甚至吹不皱水面的一股微风都足以打乱它偶然的行程,一团树叶的作用让它慢慢旋转,像经纬仪一样,在水面上转出一道细细的红圈。
在我们抬着盖茨,朝屋子走去后,园丁在不远处的草丛中发现威尔森的尸体,这场大杀戮结束了。